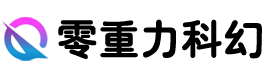作者:荒远
责任编辑:松果
本文获得第十四届衬衬杯科幻征文一等奖
维罗妮卡下定决心去死,她想了很多种死去的方式。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
1
像气泡的上升。
陈峻从恍惚中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他听见壁钟发出规律的响动,脚步声来来往往,白炽灯漂浮在天花板上,沉默地亮着。手机在兜里震动,他却不想管。
那扇门还紧紧关着。
抬头看见对面的白墙壁上,挂着一张卵细胞的横剖图。看起来就像一眸紫色的小太阳,长了难看的大黑斑。陈峻对自己说,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奇怪,就这么一豆卵泡,会变成一条鱼,一条蝾螈,接着是一只蜥蜴,最终变魔术般,会变成一对大眼睛,一段咯咯的笑声,一双沾满巧克力还会抓住你衣角的小手。
他捏了捏手里的那只鞋。小小的,毛绒的童鞋。感觉心底放松又温暖。
锁响了。
门开了。
2
木门被撞开。
带着白色面具的裸男闯门而出。枪响了,人立刻扑倒。
陈峻抓着双管猎枪从木屋里走出来。他杵着拐杖,慢悠悠把一只脚探下阶梯,站稳了,再放下了另一只。痰在喉头赫赫作响,他大声啐了一口,痰液却从嘴唇上缓缓垂悬下来,滴在衣服上。
他没有发觉。
花了很大的力气,把裸男的尸体翻了过来。他摘下了白色的面具,收在了兜里。那是一具健硕的尸体,脸上的线条刀削斧砍,现在却褶皱得像一张肮脏的手帕。嘴唇翻开,露出带血丝的黄牙紧绷着,双眼翻着白眼,一股劲想把瞳孔翻进后脑勺。手指狠狠扣进地面,留下五道细长的沟槽。
他笑了笑:“我应该等你再跑会。”
抽出了猎刀。这把猎刀看起来跟他一样陈旧了,分割骨头的时候发出令人担忧的声响。当暮日西沉,他终于把尸块全都丢下了山崖,顺着山崖下的河水流向远处。用落叶掩埋血迹后,他去检查了林地边上的壕沟和木签的拒马,果然,一个大洞肆无忌惮地敞开着。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已经老去,落满了灰尘,晦暗,甚至泛出腐朽的气息。
以至于束手无策。
等他走回木屋的门里,气喘不止。衣柜里发出乒乒砰砰的异响。好家伙,还有一只。枪托抵肩,击锤蓄势待发。他吹了一声口哨,“出来吧!伙计!”
一只面具人手脚并用地爬了出来,浑身赤裸,胸脯前两朵待放的蓓蕾告诉陈峻,这是发育中的少女。她爬到木屋的正中央,面对着他,跪坐着。她戴着的面具,洁白又小巧。
扳动扳机,卡壳了。
陈峻暗骂了一声,一掌劈开了肘击枪膛,捻出了哑火的霰弹。他虚着眼,看见底火壳上清晰地印着击针打出的凹槽。坏了,自己是不是忘了灌雷汞进去。
他看向少女,少女歪着头看着他,她像是误会了什么,开始东张西望起来,像一只第一次浮上海面的小海豹。她爬到木屋四壁的展示柜探索起来。
她碰倒了一台收音机,多米诺骨牌一样,桌上一排精致的电子产品摔在地板上。灰尘弥漫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里。
她笑出了声。
“没关系,小东西,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电了。”陈峻往枪管填进一发新的霰弹,合上枪机。
女孩没有理他,沉浸在自己的冒险里,她围绕着木屋四遭的种种收藏品,手脚并用,打破搞坏了很多工艺品。陈峻却发现,自己怎么都按不下扳机。他的臂膀隐隐作痛,大概是分割尸体过于疲惫了。终于,他放下枪,开了一瓶劣质酒。坐在扶手椅上,一口一口呷着。
当女孩接近那只小鞋子的玻璃钟罩,他又举起了枪。他忍不住说,“小东西,不要碰。”
压住扳机,闭上了眼。
哆。
哆哆。
哆哆哆。
陈峻睁开了眼。
女孩在拨弄钢琴琴键。
“啊,你喜欢这个,小东西。”
陈峻起身,走近女孩。此时女孩正张牙舞爪地砸着琴键,发出刺耳的噪声。他按住她的肩头,把她按在琴凳上。女孩轻微地挣扎了一下,便顺服了。
“很好,现在,五指张开。”
他用劲把女孩的手指一根根掰成弹钢琴的姿势,轻轻搭在琴键上。女孩想一口气按下去,被陈峻拉出了。陈峻摇了摇头,再次让女孩把手搭上去。这次,她没有按。
“真好,真好!”陈峻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些呜咽,有什么东西从脸上滑落。
他努力回想起自己曾经擅长的曲子。一匹匹贝多芬、肖邦和萧郎特却脱了缰,在思绪的草原上逃远了。最后,他只想起了一段很简单的旋律。
哆哆唆唆拉拉唆 发发咪咪瑞瑞哆
“试一试,小东西。”
哆哆唆啦西西西 瑞唆唆哆唆发哆
“不对。”陈峻摇头,按着女孩的手,十指重叠,手把手教。
他们弹了很久的小星星。直到女孩蜷缩到椅子下面,睡着了。发出了轻微的鼾声。陈峻取下了她的面具。对着睡颜自言自语。
他说。五十年前也有一个女孩,喜欢丢摔玩具,撕掉识字卡片,扯坏所有精美的图册。她本来应该变得像他一样,却永远不可能做到了。她是一个弱智。从某年某月开始,人类的所有新生儿都是弱智。他曾经希望她能学钢琴,只有弹钢琴才能让她安静下来,但是他从来不可能把她按在钢琴凳子坐一刻钟。
陈峻把女孩抱到粗呢的毯子上,盖上了一张毛毯。
他说,“我想应该去找找旧琴谱在哪里。”
是夜。陈峻被响动惊醒。他抽出垫在枕头下的猎枪,起床,拧开煤油灯。
他发现女孩惊慌失措地砸墙。
他摇头,“我就知道,我关不住一只野鸟。”
女孩看见他,脸上就淡显出一种宽慰。她用五指划过脸颊,示意陈峻,自己的面具不见了。
“且跟我来。”
地下室,陈峻熄灭煤油灯,把油倒进发电机。灯点亮了,堆积如岭的全是各种材质的面具。林林总总,密密麻麻。
“三十年。三十年了。在开始的五六年,你们还用的是金属面具。后来是塑料,现在是木材。雕刻,烘烤,涂抹上火葬后的骨灰。肌肉,面貌,耐力,灵活,都不过是一种面具。我很难忘记,在阴暗的遮庇里看见你们授予面具的夜晚,你们聚集在大山之外,在苍茫的大地上成千上万的男人哆嗦着,痉挛着,向女人的身体里喷射青春。”
他把那张小巧的面具找出来,交到女孩手里。
“我当初离群索居,在这里搭了木屋。我希望能够教导几个新人恢复理智。做了很多的努力,一无所获。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可能是在繁花深处拾起地上绚丽的蝴蝶残翅,
或者是在一夜蛙声后从水塘捞出被雄蛙扼抱溺毙的雌蛙的尸体。三十年前的此时此地,我第一次杀了一个人,尸骨就掩藏在这层层叠叠之下。”
他看着女孩,女孩已经戴上了面具,隔着这一面空白,他无从得知少女的表情。接着,他对自己说,“对啊,你又听不懂,还能有什么表情。”
他随便捡起一张面具,掸去尘埃,用手摩挲着。
“我知道你们没有任何加害我的想法。哪怕把枪口塞进你们的嘴里,你们也只会尝试把它吞下去。当我每杀掉一个人,我对自己说,他们是想威胁我的生命,或者拿走我的宝藏。然而内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不,不是这样的,当我取下面具的时候,我在寻找一种东西,一种我自己深处的东西。一直到我开始享受这种过程。这座木屋,那些五花八门的小玩意,那些所谓的人生的宝藏,不过也是一层面具,真正的藏品,就在这里,这些我自己都数不清的见他妈鬼的面具……”
猛烈地咳嗽。发电机呜咽了,地下室暗了下来。陈峻瘫坐在面具堆上,佝偻着背,水汽从稀疏的白发上发散开来。
他完全是一个颓丧的老人了。
“你走吧。”
黑暗中一只手握住了陈峻枯槁如树皮的手。把陈峻扶起来,牵着他走。
一个女声说,“跟我来。”
他已经想不起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听到别人的声音。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幻听。然而他有些站立不稳,那只手稳住了他。
上楼,推开房门,木地板吱嘎作响。
屋外,月色涂满了群峦与大地。
3
他跟着女孩走了很远。
走出了国家公园的莽莽山林,来到了曾经的城市。人类曾经存在的痕迹所剩无几,绿色植物爬上了混凝土高耸的骸骨,雨水在残垣上留下黑色的渍痕。渡鸦在锈迹斑驳的汽车顶上筑巢,雏鸟秋嘀。在杂草丛生的马路上,鹿群悠然驻足,翘起尾巴,傻傻地看着他。
一张张面具在郁郁葱葱中探出来,窥视着他和女孩,仿佛灌木丛中结出了白色的果实。
城市中心本来是广场,然而现在就是堆积成一座山的面具堆。犹如一座白色的沙山。在这种巍峨之下,数十年来陈峻的收藏就像一片落叶。面具人们从废墟中走出,爬上白山,踩过的面具流动下,索索落落。
陈峻拉过女孩,让她面对着他。用眼神说,别走了,我跟不上了。
面具无言。
果实们纷纷从灌木丛中走出,一股股白色的细流,最后汇集成一团雪亮的火焰。无数双手掌支撑在陈峻的躯背上,他回过头,却只能看见簇拥一起的面具们。
他们爬上了白山。
陈峻感到呼吸里出现了沙沙的声响,就像是风吹在贴着纸的墙上那样。他看见,白山上,睡着一汪蔚蓝的湖泊。不断有人从白色的边缘跳下,浸没进这湖泊粘稠的液体中。女孩站在岌岌可危的边缘上,面具不断地滑落进湖泊,却没有溅起一丝水花。这种诡异的现象让他浑身的骨骼都战栗起来。
“不要脱面具,求你了,小东西,不要脱面具。”
女孩脱下了面具,丢弃在这白山之上。此时月色绝好,银辉照耀在女孩的脸上,陈峻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微的绒毛。
她挥了挥手,跳了下去。
陈峻冲上边缘,双膝跪下,喉咙里传出可怖的像是在崩塌的声音,脸上耸拉的皱纹不止地颤抖着。在这蓝色深渊的映照里,他看见,女孩在逐渐溶解,溶解了,那双敲打琴键的修长的手,那张和煦的笑颜,那双眼睛。一面宽如舰船的黑色圆形慢慢地游了过来,就像这湖面上难看的瘢痕。
如果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这看起来就像在一堆面粉中打了一枚蓝色的蛋。
像被闪电击中,陈峻想起来了,他想起来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蓝色的湖泊。
这是一泡无远弗届的卵细胞。
有什么一直坚持着躯壳的东西,被猛然抽走了。
往后一倒。
4
梦。
长长的幽远的甬道。
陈峻知道这是梦,三十年来,他经常梦见这里,温暖亦如一只巨兽的胃腔。他知道,在甬道的尽头,有一个腔室等着他。光温柔地从穹顶的洞头倾泻下来,照亮了一圆地面,上面便开满了美丽的花朵。花地中央是襁褓里的婴儿,她啼哭着,等他到了,她便笑了。
等他真正来到腔室,并没有花地,光束中一台吊扇悬在空中工作着,在此之下是一张办公桌,医生坐在那头,年轻的男人坐在对面,七岁的女儿坐在男人的大腿上。在下一个瞬间,他发现自己坐在医生的对面,女儿坐在他的大腿上,鼻涕已经流到了下巴上。
他捏了捏女儿缠着纱布的小手,掏出纸巾,轻柔地拭去了鼻涕。
医生开口了。“我们做了全套的检查,你的女儿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当然,除了困扰我们全人类的那几处基因变异。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些皮肉伤不严重,我已经上了药,明后天有空带孩子来换个药。陈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明白,大夫,我不明白。今天早上在我女儿的房间,血手印,小小的,横七竖八地,一面墙上到处都是。我女儿已经七岁了,还不能上学。她有病,我了解。但是,为什么她会执着于用手挖穿一面墙,就像这面墙后面有一条路她非走不可,就像有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在遥远的地方呼唤她。医生,告诉我,这是一个智障孩子会做的事?”
“陈先生,这种情况的孩子,有些奇怪的幻想,这是很正常的。”
“不,医生,你不要敷衍我。这根本不是正常的事。这个世界就他妈该死的不正常!十年,全球都没有出生任何一个智商超过智障线的孩子。就在昨天晚上,我的所有邻居的孩子都在挖家里的墙,朝向同一个方向的墙,一个孩子直接从开了窗的墙走出去,七楼,脑子摔得稀烂。大夫,就在我来见你的路上,整个社会都乱套了。男人们在街道上打砸,女人抱着孩子的尸体恸哭,军队的装甲车放平了炮管,警察往人群的头顶发射催泪弹。大夫,你坐在这里,就给我女儿涂点碘伏缠个纱布,然后告诉我这他妈一切正常极了。”
医生摘下了眼镜,放在桌面上,叹了一口气。他说,“年轻人,我说句难听的话。就在门外,还有成千上百的家长抱着孩子,希望一进来就坐在这,候着我宣布奇迹发生。比你难缠的,我每天数不清见多少个。现在我只要支个声,就会进来两三个当兵的,把你像狗一样拎出去。你说得很对,现在全人类都急了,疯了。但是,年轻人,如果注定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堆傻子,傻子在只剩傻子的世界就活不下去了吗?”
陈峻回答不上来。
“我们搞医学的,其实比你们还要绝望。真相是,所有孩子的检查数据都正常,正常到我们都想不出敷衍人的借口。只有一个基因的点位,一个DNA上面小小的开关被激活了。
就像是一个设好的扳机,一个调好的闹钟,全球的新生儿一出娘胎便是傻子。为什么基因会这样?不知道。也许在基因看来,我们不过是它这条比线还细的核糖核酸的一层面具。有一些事情已经预备了成千上万年,我们根本不能窥见分毫。至于我们所建设的一切,语言、文字、建筑、工业、艺术、科学,不过是面具上一道道无关紧要的花纹……”
医生的声音渐渐模糊了,消弭了,周围陷入了一种绝对的安静。陈峻看见医生的嘴唇一闭一合,头顶的吊扇悄无声息地旋转着,像是一段被剪去声音的视频。接着,吊扇,医生,办公桌如同正午的水汽一样消失了。女儿站在他的面前,带着白色的面具,牵着他的手。他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如五十年前。
钢琴声响起了。
哆哆唆唆拉拉唆 发发咪咪瑞瑞哆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这一次,他用尽一生最大的力气拽住女儿的手,却怎么也抓不住。
光束外的黑暗把她裹挟了起来,迫不及待地。
陈峻坐在椅子上,倏然觉得心也像这腔室一样的空虚起来,好像飘荡在灰色的海里,变成荒无人烟的孤岛。
“……陈先生,话说到这里,也不要完全失去信心。针对你女儿的情况,我建议使用一些物理手段的感官遮蔽。比如说,给她戴上不可视物的面具,她就会认为障碍无法打破。陈先生,希望你能清醒一点,面对现实。”
你能清醒。
清醒。
醒。
5
醒来。
6
陈峻走在回木屋的路上。
面具人纷纷跪伏在他行进的道路两侧,伸出手来拉扯他的衣袖,如此这般让陈峻想起了一个很古久的故事。这让他坚定了信念,就算他的衣衫已经被手们扯光,皮肤上留下道道划痕。
尽管如此,他,一个人,行走在这苍茫的大地上,执着杖,抱着枪,就什么都不能撼动他。记忆泛滥起来。五十年前,女儿一路牵着他,走到了大山前。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再前进了。他拉过女儿,面对着她,蹲下来,摇了摇头。隔着白色的面具,他看不见她的表情。鬼使神差,他松开了手,女儿就像一只兔子一样,钻进了莽莽林野中。她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遗弃罪,他被丢进了监狱。
出狱那一天,没有任何人来接他。妻子不知所踪,父母业已去世。巨变的洪流一往无前,所剩无多的正常人退居到了大城市。城市变成小镇,小镇变成聚落,聚落终有一天会消散干净。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他伐木晾晒,支梁树栋,在高高的山崖上搭起木屋,山崖下是奔腾的河水。从城市的废墟中,精心挑选了五个男男女女。就在这木屋前的空地上,他郑重地把面具扣在了这些新人的脸上,希冀他们能逃离那远方的召唤。他用猎枪在山林中狩猎,在山顶空地鞣制兽皮。当落日西沉,五顶面具环绕着他,他抬起琴键盖板,旋律从指尖倾泻而出。
多么盼望,他已经留住他们了。
直到有一天。
傍晚,他淌着汗,喘着大气撞开房门,抬头看见墙壁上肆意放横的,是鲜血涂抹的手印。一个面具男站在那,背对着他,血从十指尖汨汨滴落,其他四个面具人蜷缩在墙角,一声未吭。他掰开击锤,用和善的语气说,乖孩子,好了,转过来让爸爸看看。
面具男转了过来。本来密合无孔的面具上,不知道用什么锐器,在眼睛的地方凿透了两个孔,血像两行泪水在面具上流淌。
诡谲,不安。
陈峻举起了枪。
7
陈峻举起了枪,指头搭在了扳机上。
他站在木屋的空地上。是时,薄雾刚刚散去,空气中有潮湿的青涩的气味,合上双手好像手心就能长出绿色的露水。风徐徐吹过山林的发梢,偶尔有不知何处树木崩裂的声响。
三个面具男,趁虚而入,用兽皮袋揣满了陈峻的藏品。他们就站在那,傻呼呼地,像鹿群一样。
看着陈峻,玻璃钟罩从口袋里露出头来,里面的那只小鞋子显得很无助。
陈峻表情淡漠,亦如四周的山岭。他用右手挥手致意,示意让面具人靠过来。
“过来,孩子,你过来。”
为首的面具人老老实实地靠了上来。“看着这里。”陈峻说,语气轻轻。他把枪口抵在了面具人的眼前。
他笑了。
“你知道吗?在这里面,藏了一个秘密。”
枪响了。
枪又响了。
劈开枪机,一抖枪身,两枚拖着烟气的弹壳抖落出来。陈峻一摸腰带,才想起,自己现在一丝不挂,子弹放在衣衫里被扯走了。啐了一口痰,他蓄了一口气,把枪甩了出去,砸倒了最后一只吓傻了的面具人。
他迈开步去,腿脚却比大肠还软。他跌倒了,跪在地面上,膝盖疼得分了家似的。吸了一口气,他伸出拳来,狠狠地砸在面具人的小脚趾。
面具人发出了断断续续地哭声。
“废物!”他骂道。“反击啊,你个废物!”
他接着砸了数拳,直到手掌失去知觉。低下头,是摔破的玻璃罩子,在残破的倒影里,他看见一个老朽的丑陋的人。皱纹像一条哈巴狗塌拉着,嘴角很没精神地向下耷拉,血混合着痰液,流满了整个胸膛。
他捡起小鞋子,捧在了手心里,毛毛扎扎的,是摩挲太久的过去。
面具人停止了哀嚎,取而代之是一种愈演愈烈的喘息。他伸出双手,疯狂撕扯着面具,颈椎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一只蝶在奋力破茧。
就是这样,没错,王八蛋。如果你想回到你那他妈该死的蓝色娘胎里。
三十年前的傍晚,一个人应声倒下,血液随着木板的缝隙浸没黑色的土地。他对着四个人说,跑吧,快跑吧,记住只有戴着面具才能留住你的小命。
三十年后的现在,他远远地丢开猎枪,掌心里是毛边的小童鞋。他对着一个惊惧发狂的人吼道,快扯下来杀我啊你个傻子!
风凝滞了。不远的树枝上,一只渡鸦睥睨着陈峻。他对渡鸦说,“真想不到,我会跟两个贼死在一起。”
面具人扯下来面具,像一头健硕的猛兽扑了过来。
在此个瞬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真正的父亲。
面具化作一弧迅猛的影子,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一挫身,渡鸦离弦而发,滑进如天鹅绒的夜空。在渡鸦无神的眼中,远峦之外庞然的蓝色在野蛮生长着,众山包围之中一名人类正在死去。它愈飞愈高,注视着这最后一个人,渐渐化成一个图腾,一个十字,一个符号。
一个句点。
© 本文版权归 荒远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及合作请联系作者。
原创文章,作者:荒远,如若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