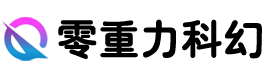作者:雷虹
虽然很喜欢科幻文学,很喜欢诗歌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但我的作品产量并不高。今年稍微有点特殊,而立之年的自己,有单行本科幻图书出版,也一如既往地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也许对于今后微不足道的写作爱好而言,算是个新的开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收到样刊样书后,自己心里会比较平静,我尝试去翻看自己写的那些已经变成铅字的文字,但很奇怪,我看不进去,一句也看不进,因为我并不缺乏去看这么一遍的时间。
这几年在把创作出的故事交给出版社之前,我已经把自己的稿子看过了不下一百遍——这毫不夸张,这其实是一直在做的事,是年少时进行科幻练笔计划时养成的习惯,只是近些年在自己创作科幻作品时这种倾向越发严重,以至于当看到这面向读者的正式文字时,心里居然开始产生一种厌倦感甚至呕吐感,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又想起高中时写下的那些文字了,那些孤独的文字。那种孤独感比我已发表过的作品《长夜未尽》里的工者93所经历的感觉更甚,是一种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却拼命坚持的癫狂,可是现在这个年龄的我已远不如从前,十六岁时的我也许真是疯了,理性而又疯狂地爱上科幻文学。
我不敢说写了那么多年科幻作品,对科学幻想文学有多么了解,从“感觉良好”到“毕恭毕敬模仿”,再到“我手写我心”,这期间的岁月流逝得很快。如若人世间的爱情能永恒该多好,生命能永恒该多好,在这样的纽带基础之上,所有的亲之情会永远延续,直到宇宙毁灭方休。说到这,有些事我不敢回头,因为我怕一回头,记忆的潮水会化成泪水,将我淹没。
年少时的我曾经会为了中国科幻文学事业而哭,为自己看不到的未来而哭,为每个人的人生如此短暂而哭,现在不想也不敢了,一想起年少的自己如此多情就不由得摇头。眼泪并不是个好东西,它只能体现柔弱。我能做的只能是不去多想,继续踽踽独行向前走。
在高中时,我把一字一画写好的各种练笔科幻故事拿给周边的人看,期待在他人看完后,我能够得到“建设性建议”,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得到的基本上都是嘲讽、伤人心的话。那让人感觉到自己是一种“小丑行为”。因此,那“极少数”几个人在我厚脸皮的要求下,花费了好些时间以自己并不怎么优秀的审稿能力帮我修稿,提些相对而言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让我在写作练笔的过程中,多少有点摸索式的收获。我很感激那几个朋友。
大学独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很多时候感觉自己是如此地不重要,那种感觉实在太糟糕,就跟寄生虫似的难以抛却。我在想自己是情操高尚者,又或是思想先进者吗?啧啧,我是吗?
我不是,我什么都不是,学业、生活残酷的现实告诉我,我什么都不配。我太过天真以至于追不上这不切实际的目标,那些目标在别人看来都似乎是轻而易举的。我曾经讨论过存在的意义,存在即是有它的意义,那我的存在,又是有什么意义呢?我就像是一个颠覆者,颠覆了自己所有的过往和决心。我并不高尚,甚至还可以扣上一个“无为”的大帽子。烦恼与我一同飞到了遥远记忆深处,飞到了一张张定格的笑脸上。
岁月无情,物是人非,“多想”只是一句“空想”。堕落的精神状况挥之不去,没有了年轻本应有的狂妄与信心。别人救不了我,我也竟处在救不了自己的地步了。我可能怀念一声清脆的巴掌了,那股使我清醒的力量、回到晨音渲染的青春跑道上来,它能使我心跳加快,两颊绯红,让我重新意识到羞耻感。因为幸福感,决不能踩在一片危险的土地上。
我靠着自己的心理调节,靠着科幻文学迷的不经意中的鼓励,最终走出了情绪的低谷,开始新的学习挑战,开始制定自己未来的目标,开始重新前行。
我知道人生不长,所以自己必须好好地过每一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主动把我的初稿稿件随意发给一个人,去获得自己的某种存在感。很多人的水平参差不齐,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我的想法很明确,我写下的文字都得是有意义的,不需要随意在别人那里得到证明,我可以做到自己证明自己。
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写作也是一样,诚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自己的稿子,我在初稿完成后才改了百来遍,就觉得要吐了,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去做出版社的编辑,不然我的每一天会很难熬。可笑的是,做一名编辑,是我年少时的理想的备选项之一。
前两年一位亲戚病故,赶去外地奔丧的时候就在想,人这一辈子时间可真不长,从小到大到老到死,数张照片便可概括。
子女们哭得稀里哗啦的,孙子辈的,则大多数时间抱着手机,一言不发,也许是不知道该干嘛吧。遗体一大早被拉去火葬场,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死人被拉去烧,也是要排队的。走廊上,满是排着队等待去烧的,阴森的过渡房,突然有了诡异的热闹氛围。附近的空气中,全部都是人的尸体烧掉的味道,身处在那种地方,即使戴着口罩,那些尸体在与高温发生充分反应后的味道,不可避免地被现场的活人吸入呼吸道,在每个人心中永久地留下那种味道的印象。
在那个时候,自己吸入的,是谁的尸体燃烧时的味道呢?谁也不清楚,只知道,那些都是来自死人的。在网上我还看到说,一些住在这种火葬场附近的居民,晾晒在外的衣服,经常会沾上空气中久久飘荡的骨灰。只有到了那种现场后,才真正开始相信网上对这类情况的描述。
亲眼看着亲戚的遗体连带着棺椁一同放在推板上,送入那个密封的锅炉里去。一想到自己活了多多少少的一辈子后,也会像这样被送入越来越“高科技”的小锅炉里,背上就发起凉来。在场的所有活人,都有这么一天吧。遗体烧了四五十分钟,再打开时,推板上的棺椁和里面的遗体,已经被烧成了细趴趴的灰了,看起来烧得倒挺干净。收骨灰的工作人员娴熟地用小扫把扫装起骨灰,子女们也忍着泪,用铁夹子捡收着未充分燃尽的大块骨头。因为一两块骨头比较大,装不进骨灰罐,工作人员夹起骨头,像敲我小时候家里烧的那种煤球一样,敲打成两三块,继续手头的封装工作,一气呵成。而那些分不清是人体还是棺椁的灰,则被全部扫进大垃圾桶了。
人在这个宇宙中、在这个地球上的三维模样、真实模样,至此不再有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烧成什么样,是一辈子之后,当事人本身所不知道的事。
我们怀化有个人修建了一个叫“怀化麻阳外星人科研站”的地方。我为此还进行了数次实地调查,撰写了探访调查录(感兴趣的可以搜索《怀化麻阳外星人科研站探访录》、《怀化麻阳外星人科研站探访录之二》)。第一次探访调查回来后不久,我从那个修外星人科研站的当事人向玉生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他研究出了“七天可治愈癌症的中药”,并且打算以四到六万或更多的价格进行零售。倘若此人真的研究出了如此神药,我想,人类离长生之路,又近了一大步了吧。呵呵,可怜,好可怜的人啊。

第一次去现场调查的时候,我就疑惑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没想到真的是为了卖药。他的新型宗教,用处是为了赚钱,为了谋私。啊,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抠门的外星人,哪有什么越编越离谱的星际菩萨大仙啊,这世界上,只有无数这种活在自己世界中,渴望有钱、渴望得利、渴望长生渴望飞升的自私的“人”罢了。
非法行医、诈骗。为这事,我向麻阳当地报了警。我看着他洋洋得意的照片。这是他的一辈子,一个他所认为的没有伤害到那些偏执精神病家庭、举债治病的穷人家庭的伟大的一辈子吧。
人生这一辈子过得可真快,看了如新周刊等媒体机构采访接触张靖平那些异能、UFO狂热者的文章,深有感触。我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这种“未解之谜”事件真的挺多的,我突然想起孩童时代,也曾多次在电视上看到张靖平、向玉生这类神秘制造者在镜头前的活跃表演,并且在自己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还好没有长大的种子。
如南方人物周刊《UFO的信徒们》和新周刊《史里芬:这些魔幻组织,坚信自己能召唤UFO》的文章所总结的那样,这些骗子的时间,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已经渐远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他们已经逐渐被这飞速开化的时代所抛弃,他们有个共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他们融入社会化的程度非常低,生活也很边缘化,是“当代社会活化石般的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历过气功热和UFO热,那段时间拎出任何一个受过体面教育的年轻人,都有可能相信气功能治病。
我们这类新时代的科学幻想者,科学主义者,很难想象有这类人存在:离群索居,和同好组成一个小团体,不断研究和强迫自己相信荒诞的事情,导致被社会边缘化20年。他们可能在社会主流视野之外,有可能无力或者无法更新自己的知识,无法获取新的、好的认知渠道,所以他们认为自己那套东西是正确的,亦或者他们内心其实知道自己认为的那套东西是不正确的,但他们因为普遍的谋私的目的,希望旁人相信他们所认为的正确是正确的。他们渴望操纵,就像偏执狂希特勒渴望操纵整个世界一样。
有时候一想,这是他们余生会做的事,这是他们余生只能做的事,这是他们在人生中,唯一可做的事,唯一的快乐吧……
这个时候,一股同情之情便在自己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涌上来了。说实在话,这是自己突然真正发自内心地同情这类人,我竟然在同情这些诈骗分子,同情这些利用公共资源谋私的人,同情这些人的人生。这些过去时代的“活化石”们也终有一死。其中一些人坚信自己能飞天,并且被人立像,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有一次,我问某个认识了近十年的、和我年龄相仿的科幻迷朋友,“怎么我最近写的一篇初稿还没帮我看,还没提出意见”,并且准备把自己心心念念的《星之继承者》三部曲推给她,这是圈内出版社推的算得上优秀的“网红”科幻文学小说。谁知,她几乎哭了——她在医院,准备做一个比较大的肿瘤手术,目前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还说如果是恶性,之后也就没机会再看我的小说了,也没机会再看科幻了,这使得这一两年来心情本就不好的我心情更加差劲。
“手术后,一定没事的,”我说,“手术完之后,还要仔细读完它们……我们还要一起聊聊读后感。”自己的眼泪还是有点控制不住。当时又看了一眼目前仍然没被封号的麻阳外星人科研站修建者向玉生的微信公众号——呵呵,如果向玉生行骗所称的外星治癌“神药”真的存在,那该多好。
好在这位科幻迷身体后来没有什么大碍。最近我还邀请对方为我要出的书写了评论文,它将随书出版。曾经觉得自己就是在“写故事”,把简单的故事写出来满足自己就好了;上大学后这样的情绪随着自己第一次获奖而有所改变。那时觉得科幻作家应当是借着科幻的时空舞台努力写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对这个世界和宇宙的看法,写渺小的生命,并且希望人类文明能够一直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好。这大概回答了我年少时“什么是我的科幻理想,什么是我心目中中国科幻的理想”这个疑问。
我现在致力于创作基于相同世界观的中篇系列故事,这纯属某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当年我携一个短篇作品参加某个圈内的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但是那篇小说,很意外地没有进入“结集”的待遇,于是,那本以比赛名为整个集子名称的书,唯独少收录了这篇一等奖的作品。我很不理解,心情很不好。我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时常翻着那篇故事的稿件,觉得它如果有人的情感,应该会很“失落”吧,它就像我一样,不会得到谁的理解,不会得到谁的青睐,是孤独的。
我不想让它那样孤独,于是我进一步完善和延伸了它的世界观,让它灵活地无限拓展开去——《星空与墙》《长夜未尽》,以及即将出版发行的图书《母塔之下》、更多的其他待发刊的系列故事,便是它的孩子之一。是的,之一。这样的世界观,对我而言,是一笔意外收获了。如若当初那个一等奖短篇,就那样进了那么一个普通合集的书里面去,那么对我而言,就不会有之后的大世界观,之后那些永远写不完的新鲜故事了。感谢命运,感谢缘分,感谢一切。
科幻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不可能再被他人的言语所轻易影响。当我看到我写下的文字时,某些时刻我惊奇地发现,它们既熟悉又陌生,那会儿我想起了科幻作家刘慈欣大概说的话:当你的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它们就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了。是的,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我是应该感谢年少的我吗,让我写出这么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奇怪怪的文字?
星海的波涛依旧汹涌澎湃,我的梦邸还在前方。晨曦之音如雾般缭绕,人生信仰定不能潦草!
我将在时间的长河中,继续与科幻一同前行。
2023年3月31日

原创文章,作者:我与科幻专栏小编,如若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