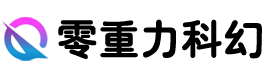我自幼生活在这个村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双亲便去世了。爷爷奶奶好不容易将我拉扯到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结果他们也相继去了那个世界。
无依无靠的我,家中的田地很快便被村霸占用了。我只能在同村人的冷眼和嘲弄中,靠捡些废品、帮其他人家打打零工挣点生活费用。到了快结婚的年龄,我也因为家里太穷,没有姑娘肯跟我,所以我倒是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光棍之一。
如果没有那件事的发生,我可能会这样慢慢老去,平平淡淡地过完这糟糕的一生,直至化作后山树林的一滩养分。
具体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突然发现,每一个出现在我视线中的动物,它们的头上都顶着一个数字。
最开始我非常害怕,以为自己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盯上了。不过在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些数字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于是我开始尝试搞清楚这些数字的意思。我没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因为别人只会把这当成是老光棍的笑柄。
在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验证,令我狂喜的是,我所看到的这些数字竟然都是这些动物的死期倒计时!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能力,但在我的一番装饰下,没过多久,我赫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半仙”。
原先对我嗤之以鼻的同村人一下子对我恭敬了起来,那谦卑的态度,仿佛下一秒钟就要匍匐在地向我叩拜。他们争先恐后地往我家中送吃的、喝的、用的,更有甚者还帮我重新砌了几户瓦房,在他们的热情下,我从原先骨瘦如柴的腌臜老头变成了一位体态丰盈的老爷子。
不过,我并不感激他们,相反,我厌恶他们到了极点。
随着日子的推移,我的能力被我用得更加得心应手,虽偶有失误,倒也无伤大雅。可遗憾的是,我看不到人的死期。每当有人来问我诸如所剩阳寿之事时,都被我用“天机不可泄露”等装模作样的话术给打发走了。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能看到别人头顶的数字了!那人不是我们村的村民,而是小张的爸妈捡回来的一个流浪汉。他们这对老夫妻真是好人,经常做善事不说,还从来没有瞧不起我过。
但奇怪的是,当他们像往常一样要将这位流浪汉送到城里的救助机构时,在村口偶遇他们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流浪汉头顶的数字,从之前的3689变成了1。
二人脸上噙着淡淡的笑意,慢慢地朝我的方向走来:“老半仙,溜达呢?”
“张老哥,张嫂。”我顿了顿,瞥了一眼那个被他俩拾掇干净的流浪汉,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呢?送人去城里?”
他俩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的目光来回在三人身上扫视着,心中万分纠结。这对夫妻脸上和善的神色逐渐被疑惑取代,他俩对视一眼,张老哥问我:“你怎么了?”
我不再犹豫,将他俩支到一旁,小声道:“老哥,张嫂。这个流浪汉恐怕活不过今天了……”
“什么!”他俩吃了一惊,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我叹了口气,轻轻地点了点头。我有些不忍,又扭过头看了一眼那位流浪汉。
在我扭头的一瞬间,一股寒意猛地向我的背后袭来,我急忙回头望去——夫妻俩仍惊讶地看着我,不过在他们的眼神中,仿佛还蕴含着一丝阴毒的味道。
我打了个冷颤,尴尬地向他们笑了笑,道了个别,然后快步离开了这里。
背后那两道怪异的目光,一直紧紧地跟随着我,直到我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回到家中后,我坐在床边,努力地平息那颗狂跳的心。
“咯咯哒……”一阵叫声将我从奇怪的想法中拉回了现实,原来太阳都快落山了。我向院中看去,鸡笼里的某只母鸡顶着一个黑漆漆的“562”,正兴奋地用它的叫声向我报喜。
这些鸡是同村人为了讨好我送给我的。听着这只母鸡的声音,我的心中厌烦不已。鸡鸣声不住地向我耳中侵蚀,我终是忍耐不住,决定将这只鸡宰了炖食。
我面色不善地向鸡笼走去,但走到一半时,我刹住了脚步——那只母鸡似是感觉到了危险,向后移了几步,它头上数字的后三位,却是变得有些许模糊。
我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一股不安的低咽从母鸡的嗓间发出,而它头顶的数字,也彻底转变为了漆黑的1!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所震惊,一股不详的念头止不住地钻入我的脑中。我害怕了,我不敢与那只鸡对视,它眼中的警惕如同针尖般刺入了我的心田。
“老半仙?老半仙!”我被突如其来的招呼吓了一跳,但待我看清了打招呼的人时,我更是情不自禁地退后了一大步。
夫妻俩的脸上依旧挂着那一成不变的笑容:“怎么了老半仙?发什么愣呢?”张嫂说罢,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大块肉。“这是我们之前从镇上切的牛肉,送一块给你。”
“谢谢……谢谢嫂子……”我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不用了……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我们切了很多,家里还有好几十斤呢。”张嫂那宛如恶魔般的低语无情地钻入我的耳中。
剧烈的恶心从我的胃中翻涌至喉头,我再也无法忍受,冲进了院中的厕所里,狠狠地关上了门。但是,我却用双手捂紧嘴巴,不敢发出半分声响,因为,我分明透过门缝看到了他们面容上的狠厉之色!
是夜,我做了一场噩梦,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床铺。
第二天早上,一夜难眠的我还未下床,就听到门外喧闹的动静。我推开门,发现院中聚集了很多村民,个个手中都或多或少拎着一些礼品,有几个人的头顶上,还漂浮着一些可怜的数字。
我发疯似的冲进屋里,抄起一根木棒,把他们统统赶走。然后我将大门关紧,打开了屋内所有的灯。我惊惧地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颤抖地喘着粗气。
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我的腿脚早已麻了,肚中也空空作响。我尝试站起,却没站稳摔倒在地,撞到了一旁的柜子上。我疼得龇牙咧嘴,扶着柜子缓缓地站起。
就在起身的那一刻,我扭头看向了柜子上的镜子,镜中那张憔悴的面孔,头顶上居然也跳出了一个所剩无几的倒计时。
当夜,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吃人的村子。
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城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陌生,我的衣着老旧且过时,与大街上的灯红酒绿格格不入。况且我的年事已高,除了招摇撞骗外,身上更是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加之这些年来又过惯了安逸的日子,如果不找个合适的去处,恐怕要不了多久,我就得横尸街头。
好在我的身上还是有一些积蓄,于是,在几位出租车司机或嫌弃或同情的表情中,我跑遍了城中的福利机构,最终在缴纳了费用后,住进了位于郊区的某一家敬老院。
这家敬老院傍山而建,远离了城市的聒噪,不过里面的配套一应俱全,健身器材、小公园、诊所等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个人工开凿的湖泊,供大家任意垂钓。
我是第三个住进宿舍的,其他两位分别是一个坐轮椅的哑巴,以及一名精神有些异常的“老疯子”。
一开始我不愿和那位老疯子同住一屋,不过在前几天的紧张过后,我发现老疯子除了行为怪异一些,其他倒也没什么异常,如果不理睬他,他倒也不会主动去招惹别人。
而那位哑巴,却让我羡慕不已。他的儿子每个星期都会拎着一堆补品过来看望他,推着轮椅陪他在外面走走,和他说一些最近的趣事。我听别人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儿子的工作太忙,实在无法照顾到他,他这会儿应该在城里享清福。
要是能一直在这里安稳地度过余生也挺不错,可惜天不遂人愿。没过多久,负责我的护工就越来越没有耐心。
起初,我还以为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惹她不高兴了,每次她有情绪或者大声说话时,我都会向她道歉。可我一次次的退让换来的是她的变本加厉,她发火的频次愈来愈高,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冷漠,到最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引起她的怒火,她甚至还对我动起了手。
我不敢反抗,也无法反抗,我没有家人为我做主,我自己的大部分积蓄也都当做护理费交给了他们。
某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被那位护工掐伤的胳膊仍隐隐作痛。
忽然,隔壁床铺发出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待我扭过头去,一个黑漆漆的身影豁然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
我被吓得往后一缩,我使劲眨了眨眼,看清了这个身影的主人——原来是老疯子。
“疼吗?”还未等我说话,老疯子主动问道。
“什么?”
“我都看到了,那个护工又动手打你了吧。”
回应他的是一阵沉默,我没有开口否认。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都看到了。”他顿了顿,补充道:“你被他们的花言巧语骗了,这里根本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好。”说完这话,老疯子又折回了他的床位。
一个小盒子轻轻地砸落在我的身上,我将其捡了起来。
“药膏,对伤口恢复有好处。”老疯子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妹没一会儿鼾声便从他的方向传来。
这老疯子,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疯?
有一天,我在外面溜达,发现哑巴正坐着轮椅在晒太阳。
“老哥,晒太阳啊。”我走过去打招呼
他朝我露出一个笑容。
“要不要一起去‘走走’?”
他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我默默地在后面推着他,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在小路上闲逛。阳光肆意地倾洒在我身上,将这几天心中的阴霾也祛除了大半,我的心情不由大好。我对哑巴说:“老哥,今儿天不错,咱们去湖边逛逛吧。”
可谁知我话音刚落,哑巴便浑身颤抖,嘴巴里发出不正常的“唔唔”声,他猛然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一副害怕的表情,手舞足蹈,在空中胡乱地比划。
我完全看不懂他的意思,疑惑地看着他。
哑巴犹豫了一会儿,把心一横,掀开了他的衣服。
“啊!”我被吓得连退几步。哑巴的身上,竟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半月型红印。
我站在原地,盯着哑巴身上那些可怕的伤口,完全不知所措
“178号!178号!”一个略带愠怒的声音钻入我的耳中。
一名护工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一边走一边数落着:“你不知道今天上午要体检啊!你要带这哑巴上哪?出了事你负责吗!”
我没有说话,生怕又惹来她另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只是尴尬地朝她笑了笑。
她投来一个厌恶的眼神,重重地哼了一下
护工的怒气没有因为我的沉默而消散,下午她给我重新安排了体检,可做那些项目时,医生故意加大了手上的力度,前阵子身上恢复得差不多的伤口,在这暴力的检查下,又重新渗出了丝丝血迹。
那天晚上,我疼得根本睡不着,稍微动弹一下都得倒吸一口凉气。
“又被他们欺负了?”老疯子翻了个面,向我问道。
“唉……”回应他的是我无奈的叹息。
“你越让着他们,他们越得寸进尺。”
“可像我这样无依无靠又没钱的人,又能怎么办呢?”
老疯子不屑地嗤了一声:“有依靠又能怎样,那帮护工只想着捞钱,很多子女对他们的爹妈不管不顾,甚至巴不得他们爹妈早点死,这他妈就是个吃人的鬼地方!不信你看……”他忽然止住,不再言语。
不正常的沉默笼罩着我俩,老疯子就在这种氛围里进入了梦乡,可我却依旧睡不着,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他不像是疯子,难道是我疯了? 有机会我一定要再请教请教他。
可惜,我再也等不到这个机会了。某天中午我从外面回来后,发现老疯子不见了。我到处打听后得知,上午他和护工爆发了一通激烈的争吵,然后来了一帮穿防护服的人把他带走了。
下午,我们就收到了他突发恶疾,经抢救无效去世的消息。
我双目无神地看着空荡荡的床铺,一股悲凉涌上心头。
忽然,老疯子枕头下有一抹色彩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走到跟前,将那个物件抽了出来——原来是一张敬老院所有人的大合影。
照片上的老疯子笑得极为灿烂,没有半分疯癫的样子,他的旁边站着一名和他年龄相仿的女性,看起来应该是他的妻子。我随意地在照片上扫视了一眼,正当我准备将照片塞回他的枕头下时,我的余光瞥见了两个非常熟悉的身影。
那两人和院长站在一起,微笑地看着前方。我死死地盯着照片中的那两人,双手忍不住地剧颤——竟然是老张的父母!
如同抓住了一块烙红的铁,我吓得把照片扔在地上,然后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躲进了被窝里,任由冷汗打湿我的全身。
又是一个未眠的夜。
第二日是周六,一大清早,哑巴的儿子就拎了一堆礼品来探望。和我点头招呼之后,他将哑巴推了出去。
待到他们远去,门外再没有丁点动静时,我起身下床,来到了那一堆精美的零食糕点前,一件又一件地搜寻着包装盒上印制的日期。
做完这一切后,我也离开房间,向人工湖的方向走去。
哑巴父子早已抵达此处,二人一坐一站,静静地盯着湖面。哑巴手里捧着一块糕点,他儿子则在为他揉捏肩膀。
没有同他们打招呼,我踱步至湖边,看向了湖面。湖面上倒影那不停变化着的数字嚣张地射向我的眼,微觉刺痛的我忍不住将目光移至哑巴父子。
哑巴面带痛苦地咬了一口早已过期、长满霉菌的糕点,而哑巴的儿子却是面无表情地继续为哑巴按摩,只不过他手中的力道和指尖的腥红,似是又深了几分。
哑巴的儿子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他扭过头来,露出了一个阴森的笑容。
而我瞥了一眼哑巴头上那缓慢减少的数字,也朝他们露出了一口黄牙。
“178号!178号!又死哪儿去了!”护工那毫不掩饰的咒骂钻入了我的耳中。
我没有立刻回应护工,而是再次低头看向湖面,老疯子之前所说的话,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和心间游荡。
终于,我下定了某种决心,抬起了头。
“178号?178号!”护工的声音愈发尖锐。
“哎哎,我在这儿呢!”我换上了一副虚伪且阴毒的笑容,转过身去,右手使劲地向护工挥了挥手,左手则紧捏着一把锋利的刀片。
湖中倒影上的数字,随着我的动作而彻底定格。天上那如同千年前一般灿烂的烈日照射在我脸上,似是闪耀过一阵诡异的光……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零重力科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0gsf.com/a/1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