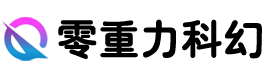作者:莫名
本文获得第一届零重力科幻评论比赛一等奖
序
韩松是我第二个接触的科幻作家,第一个是刘慈欣。最初读到他的作品是在一个网站上,我记得那部作品是《地铁惊变》,它给我一种完全迥异于三体的阅读体验,而在此前,我一直以为科幻小说都是三体式的。
刘慈欣评论他的作品比自己的多出一维,这是很恰当的比喻。韩松的作品不是简单的二维图画,它隐藏了不可见的维度。在《三体》中,刘慈欣曾对四维空间作出详细的描写,也就是将原本不可见的东西化为可见的,韩松却恰恰相反,他用种种悖论般的情节营造了一个巨大的高维迷宫,透过这些悖论的裂缝,读者仿佛瞥见了那处在可见世界及其规律之下更为隐蔽、深刻却又不可见的东西。那是一种人类的思维无法揣度的不可言说的神秘。在他的早期作品里,这种神秘偶尔会以饱含激情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宇宙墓碑》和《红色海洋》第一部的末尾,那是一种热烈的悲哀,洋溢着令人绝望的宿命感。
韩松似乎不适合写长篇,他的《红色海洋》、《地铁》是由当初零散发表的作品整理出来的,经过修改使其前后连贯之后,反而丧失了原本的韵味。或许他当初的确有一个完整的构想,但这构想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陌生,直到它的创造者也记不起那时的感受,如同面对着另一个人的文字。这是他的职业使然,碎片化的时间只能碎片化的写作,因此他的作品比起小说更近似于寓言。他仅有的一部长篇《火星照耀美国》,虽然保持了情节的连贯,却淡化了那种独特的神秘感,或许碎片更适合呈现存在的吊诡。刘慈欣说读了韩松的作品像被划开一道伤口——的确,一部完整的作品、一个体系或许会崇高,但绝不会神秘。只有碎片,它划开可见的世界,让后者成为象征。
我尝试用我贫乏的知识“解读”一下韩松的作品——当然,这算不上真正的解读,不过是我自己肤浅的理解罢了。但我想,任何一部作品之所以深刻,正在于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意图是不可穷尽的,也就是,能被无限的解读下去。那么,即便是肤浅的理解,对于作品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韩松作品中的性别隐喻
男人是容易被考察的,女人却并不泄露自己的秘密。——康德《实用人类学》
性别问题几乎贯穿了韩松的所有作品,从《宇宙墓碑》中的阿羽到《亡灵》中的夏泉,他的作品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对女性的恐惧。恐惧意味着在自我中感受到他者的存在,女性便是这样一个他者。她一方面是与人类最亲近的母亲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令人感到陌生。因为女性一向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她们的性格捉摸不定,而且比男性更会隐藏自己。尼采曾说,“从女人那里,你了解不到女人的任何东西”。相比于女性,男性似乎更易考察。如果说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这世界的两极,那么男性就象征了被展开、被观察的一面;而在女性身上,人们则看见了世界本身的不可知。正是这一点,女性才令人恐惧。
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两只小鸟》和《冷战与信使》中曾经出现。在那里,女性是陌生的。我们熟悉她,但并不理解她。女性是处于理解之外的存在。我们同她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这种暧昧中包含了恐惧。
这在《红色海洋》的受控环一章中也有体现,当机器人超出控制论专家的预料,表现自己的智慧时,韩松作了如下描述——
“机器人眼神迷离,用女人般的声调说”。
机器人对于人类是他者性的存在,但它也同样是与人类相似的存在。机器人隐藏了自己,这令控制论专家发觉自己对这机器人实际上是陌生的。他感到可怕。这种无法捉摸的特性,和韩松其它作品中的女性很像。于是,在这章的末尾“机器人的眉宇间浮上一层愁云。这时,他想到了性别的问题”。
但这仅就性别作为纯粹的概念来说是这样,事实上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掺杂着男性和女性的要素。性别本身很可能先于生命的性别之分存在着,并同一些终极的问题相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性别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韩松在《脱母运动》中甚至这样写道——
“宇宙中有三种箭头,都不可逆转。一种是热力学的箭头,方向是从有序到无序;一种是心理学的箭头,方向是从事件的感知到事件的记忆;一种是因果的箭头,方向是从原因到结果。外星使者指出还有第四种箭头,那就是性的箭头,方向是从雄性到雌性。这个箭头是更为基本的箭头,也就是说,它统率着其他三个箭头。”
而在《红色海洋》中,韩松则借主角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观点:“海洋本身的性别,其实就是女性”,“海洋变得不近人情并且仇视起生命来。原先,它或许曾用少女的爱情为这颗星球孕育出第一线生机,现在它更像一个不能生育的老女人,进入了烦怨一切的更年期,连自己的孩子也要吃掉”。这正像是荣格的大母神——那所有女性和母亲的原型——她既孕育一切,又吞噬一切。
毫无疑问,女性比男性更深,正像母神比父神更强大。在荣格看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父神仰赖的是意识,母神根植于潜意识。因此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的偏见,认为女性缺乏意识。女性实际上象征了一种混沌的冲动,在母神面前,父神是渺小的。女性是世界实际的君王,因为“真正的主人,是比猛禽更为低姿态的两只小鸟”。
在韩松的作品中,女性正是对这世界的诡秘性本身的隐喻。在男性与女性的距离之间,存在着人与世界本身的距离。
二、韩松作品中的时间性
人在根源上是时间性的存在。——海德格尔
时间有两种,一种是物理上的时间,另一种则是作为体验的、心理上的时间。对人而言,后者更为基础,而且两者并不总是一致。比如说,我们常常认为童年的时光较成年的时间更漫长,或者当我们来到一个陌生场所时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然而一旦熟悉了,时间就会加快。在这两个例子中,物理上的时间都没有变动,心理上的时间却可短可长。
在韩松的作品中,时间性往往是沉默的。这主要体现在《红色海洋》和《没有答案的航程》中,而对于前者,时间问题也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一条线索——
“在深海里,因为水压的缘故,大多数人类成员忘性很大,只能记起不久前的事情。”
没有人会否认,心理上的时间和记忆密不可分。对水栖人而言,他们或许并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对食物的欲望。
叔本华认为,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在于,动物只生活在现在,人类还在概念中拥有过去和未来。按照这种说法,海栖人,这种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悲哀而奇特的生命,似乎更偏向于动物。
在韩松的海洋中不仅没有记忆,也没有昼夜和四季,除了一望无际的红彤彤的海水,便只剩下巨大的空虚。按照《没有答案的航程》中的话说,就是“没有白昼和黑夜,时间便像盲流”。时间在韩松的作品中不仅是沉默的,甚至是被杀死了的。
德国哲学家谢林曾经提出过史前时间的概念,在那里“没有真实的时间相继,这并不是说在它自身之中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在史前时间中,当然也有日出日落,人们也是晚睡早起,有娶有嫁,有生有死。但在这里没有持续,因而也没有历史。这就像一个个体,在其生命中昨天与今天一样,今天与昨天一样,他的此在总是一个反复交替的重复的圆圈,没有什么历史。”
这正像是韩松笔下的水栖人,他们活着,却没有历史。如果说历史是对时间的自觉,那么水栖人就是单纯的沉湎于时间之中,因而不曾拥有时间。韩松在受控环一章中借文化大臣的口这样说道——
“你又谈到时间了。这是你残存陆生基因过强的显示。这不好。还是让我们忘了时间吧。生命如水之循环,世界本是幻影。”
这似乎是东方文化的特点,而受控环中文明两极中的肉身文明,也更近似于东方。韩松曾在《时间回旋》的评论说,汉语没有时态,这是与英语显著的不同。诚然,我们的历史记载比其它文明都要悠久,但我并不拥有历史。我们的文明总是在不断的轮回,却始终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诞生。黑格尔甚至这样说,“世界历史从中国开端,但中国却在历史之外”。而谢林则断定中国正是那古老的史前时间的遗迹,是一具僵尸。
这种时间性的死亡,延伸为了历史本身的断裂与歧异。这在《宇宙墓碑》、《红色海洋》、《天道》中都可以看到。实际上,历史本身也是很可疑的概念。或许,它仅仅是人类受限于自己生存的空间形成的幻觉。叔本华把历史定义为“人类漫长而又艰深的迷梦”,这句话也是韩松作品中历史的写照。
《天道》中的一段话最适合做总结——
“时间的潮水蚀掉了一切因果维系。超新星爆发,太空时代,探索宇宙的人,一切往事的投影徒然落在了往事的往事上,而现时的人都按现时的观念去解释将来。”
三、韩松与悲观主义
一个人若是连希望都放弃了,那他就不会有害怕了,这才是“绝望”这个词的意思。——叔本华
罗伯特·索耶说,悲观主义者总是显得很聪明。这话其实是很乐观的。基尔克果认为,绝望的诸形态中最低级的,是感受不到自己绝望的绝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乐观主义者是最绝望的。
韩松很难称之为一个悲观主义者(虽然他在访谈里说自己有点悲观),但他一定是一个“绝望主义者”,甚至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他的作品弥漫着一种无所不在却又看不见的虚无,一种巨大的缺失却又说不出缺失什么的郁结。如果说早年这种绝望曾以热烈的方式展现,那么如今就只剩下一种癫痫般的绝望,一种绝对的虚无。
除去他作品中政治寓言的部分,韩松作品的特点在于,有一种诺斯替主义的被抛性和对这个世界本身的陌生感在里面。他的作品触及了人类面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感受。他常常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抛到一个陌生荒诞的地方,并能够生动的描绘出那些人物面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行动。他仿佛在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俯瞰着这个世界,因此他的作品有一种超脱时代的气质,尽管它的内容却恰恰映射着现实。他笔下的历史也是多维的,有一种超越了此世的深邃,刘慈欣的作品虽然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史诗感,却仅仅是一幅画得很好的二维图像。我认为这是韩松作品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
韩松有这方面的天赋,从他初中时期的作品,便弥漫着这种诡谲的气息,我以为这种气息是天生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宇宙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在《符号》中,也有这样一段对话——
“喂,提到宇宙,你想到了什么呢?”
女孩暂停了对满嘴纸杯碎屑的咀嚼,略微想了一想,吐出一个词:“别扭。”
如同小说中认为的,这个词汇虽然朴实,但的确是再贴切不过的词汇。宇宙有这么一种别扭,它无法被分析出来,而只能被“瞥见”,一旦正视又归于消逝,不可捉摸,就好像精神分析中的“原质”,是说不出的。那是一种如鲠在喉的感受。
这种感受也在人那里体现出来,他在访谈中说,“人也是宇宙的一个缩影,别扭”,“人在宇宙中是很奇怪的一个存在……就是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么一种东西出来?人类的位置也就是跟这个为什么有关系,宇宙最开始可以不创造这样一种东西,宇宙也能成立的,为什么偏偏要这样?”
这就好像加缪的那句话,“荒谬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人与世界的共存”。把世界换成宇宙也很合适。不过在韩松的作品中,人不仅对宇宙,对与宇宙的共存,并且对自己作为人的现实也困惑不已。
笔者在初中的时候曾有过相似的体验。某一天的夜晚,我突然为自己出生在地球,为自己作为人类,为自己作为自己困惑不已。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因为这种偶然性是不可解释的。
这些无法解释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对荒谬的体验。这种荒谬的体验意味着意义的缺失,也加重了他悲观的情绪。
在他近期的作品《亡灵》中,他写道,“宇宙中的生命不可能跨越时空互相访问。技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毁灭了”,“再高级的技术到了最后,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绝望的。”——比起黑暗森林,这或许是更悲观的看法。
四、韩松与思辨实在论——科学外幻想
不规则足以废除科学,但不足以消除知觉。——甘丹·梅亚苏
思辨实在论是新兴的哲学思潮,比起传统哲学,它和科幻更具亲缘性。它的发起者之一,甘丹·梅亚苏,受休谟影响试图从哲学角度论证物理规律的可变性。在这种哲学中,物理规律仅仅是浮在世界表面上的波纹,它的深层则是恐怖的超混沌。这意味着物理规律被更改的同时,也可以维持世界的可知觉性——而这曾经被康德论证为不可能的。由此,他提出了科外幻小说的概念,在这类小说的世界里,不可能构建起任何规律,因为谁也不知道这规律在下一秒会不会失效。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三体》中的规律武器,实际上不仅仅是设定,思辨实在论在理念上也和《三体》也颇相似。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是偶然性的哲学,它认为惟一必然的就是偶然性。这意味着思维是偶然诞生的,而这是通过近代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发展得到揭示的。因为通过数学,思维可以思考自己不存在的世界。这把思维丢进了无意义的深渊中去——宇宙与思维漠不相干,它什么都不意味。在这里,思维发出的任何质问,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
不过比起刘慈欣,或许韩松的作品更符合甘丹·梅亚苏对科外幻的定义,最明显的就是那篇《热乎乎的平衡》。很明显,这是对汤姆·戈德温《冷酷的平衡》带有戏谑味道的仿效。
在这篇文章中,韩松展现出了一如既往的神秘感。先是船上突然出现了偷乘者,那是一名少女,不过在“我”和少女做过之后,原本冷酷的方程式似乎因为“我”的选择而发生了神秘的变化,
“船的航向已经自动改变了。而用了三十多年的仪表盘也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一个崭新的家伙。船舱中的其它布置也发生了许多古怪的变化,飞船已不是我熟悉的那艘了。”
而这都是因为“宇宙中出现了偷乘者”,于是“世界向我展示了无限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究竟隐喻了什么暂且不谈,但可以看到的是,规律确实改变了,而且是突然改变了,不是受到了其它文明的修改,或者神的恶作剧。尽管构建梅亚苏口中的科外幻世界观可能并不是韩松有意为之,但他的作品确实符合这个定义。
韩松的作品是科学外幻想,在他的作品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了。他在挑战可能性的边界。他的世界是科学外的世界,在这里,不规则废除了科学,却没有废除知觉。而这才是真正神秘的。因为惟一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之事确实发生了。不可思议之事本身并不神秘,而它的发生,才是神秘的。这意味着一种藏在表面的规律之下更深的东西,不过那不是超混沌,而是世界本身的不可捉摸,它始终在规律之外,因此才显得意味深长。
或许,它就是这世界的神秘本身。
五、韩松与佛教
一物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龙树
除了性别问题,在韩松作品中比重最大的恐怕就是佛教。无论是早期的《逃出忧山》还是最近的《医院》三部曲,佛教色彩都很浓。他的《劫》甚至直接就是一部以佛教为题材的时间旅行小说。
佛教是消极的宗教。对佛教徒来说,世界就犹如眼疾之人妄见的幻影,本来不生,也无根由。眼疾一除,佛性便显,方觉本无一物,空空如也。黑格尔说佛教是“自在的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得很对,它缺少自为的环节。佛教将整个现象世界视为虚妄的,不仅本体论上如此,知识论上也如此。韩松或许是受佛教影响,很喜欢用幻影、梦幻,如假包换之类的词语。在《地铁》系列的结局中,主人公之一的雾水最终发现一切都不存在,也是颇具佛教色彩的结尾。或许是韩松本人的职业和性格,使他体验到了那种“一切皆空”的幻灭感。
佛教的成分也散见于他的其它作品中,比如《驱魔》中的叙事代入疗法,实际上暗示了一种缘起观,因为根本没有故事发生。
或者《噶赞寺的转经筒》,那转经筒就像苏格拉底的镜子,转动一周,便将整个宇宙纳入其中。因此说“在那转经筒中,有一个跟我们这个宇宙一样的宇宙”。而在结尾中,转经筒被砍成两半,里面空空如也,却直接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宇宙大爆炸”。
以及《闪光·阉割》中的因明学,实际上是佛教的逻辑学,但很难看出和文章内容有什么关系。
不过韩松笔下的佛教,更多的却是呈现出一种诡谲的色彩,以及一丝戏谑。笔者曾经一度对佛像感到恐惧,因为笔者总是觉得佛像的笑有些诡异。而在《逃出忧山》的结尾,韩松笔下的佛像也呈现出了同样的诡异——
“妻子手中这一尊佛像也在着迷地观看外面的景色,它简直就像他与她生育的一个婴孩。这孩子长得贪婪又肥胖。小家伙的嘴角还挂着一丝讥笑呢。”
如果说在《劫》中佛陀的悟道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那在这篇文章中,大佛本身也陷入了谜团之中,“原来他即是佛。而佛又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存在于心也已很久了,而他竟然多年来糊涂忘却,没再追究。”
韩松作品中的佛陀往往是一个旁观者,面对这个诡谲的世界,佛陀的笑反而显得诡异,仿佛讥笑。他是“慈悲而冷漠”的。
或许《医院》开篇中的一句话更符合佛教本身——
“一切本无问题,也无答案”
六、结语
将不可见的东西描绘出来,是崇高;而把可见世界作为象征来显示那不可见的,则是神秘。从某种意义上,显示比描绘更难。
韩松曾用一种悲观的语气说道,“大脑是宇宙的产物,要靠人的大脑彻底弄清宇宙,最终是一个悖论。”
这是一个康德式的观点,也是科幻的永恒主题——有限物和无限物、人和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
如果说刘慈欣写出的是有限物面对无限物时感受到的崇高,那么韩松则针对这种裂缝本身。这两个人一同构成了中国科幻的两极。
© 本文版权归 莫名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及合作请联系作者。
原创文章,作者:莫名,如若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