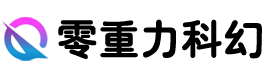作者:荒远
责任编辑:瓦力
导读:我是商陆,现在是一台汽水售卖机,兼职商陆的备份记忆体。我的旁边是一台口香糖售卖机,她曾经是我的爱人周茜。每天我们都会一起在船上看日出日落。只有在梦中我才会和她拥抱在一起……
在那东西爆炸以后,在美国能够用一颗炸弹摧毁一座城市的设想已成定局之后,一位科学家转向父亲,说: ‘科学现在与罪恶携手了。' 你知道父亲说什么? 他说: ‘罪恶是什么东西?’——《猫的摇篮》
1.
很难忘记那个炎热的下午,街岸上行人寥寥,码头上站着荷枪实弹的宪兵,空气中有一股若即若离的天然气臭味。我坐在省医院的门口,把身体里多处合成肌肉的液压泄了,像一条脱了毛的迟暮的狗。几个狐朋狗友扬了扬手里报告单,挤眉弄眼向我走过来。那个天灵盖开花,顶个机械头的叫商陆,他贼笑着对我说,“小子你福分不浅啊,打算装个多少公分的家伙式?”
“成了?”我坐直了身子。肌肉开始智能升压。
“哥们我的手段都信不过?以现在的行情,你能装个石墨烯的。当然,怕用力过猛,折了,仿生材硅胶也成,就是假了点。自带润滑的五十万起底,没润滑的三十万,回去叫你爸妈掏钱。老人家俩一高兴说不定给你装两具,还买具压在婚床枕头下备用呢。毕竟,能把种保下来也是你的本事。哥几个说是不是。”
商陆合上他仅存的臭嘴,几个没心眼的残废又哄笑起来,有怪叫保睾有方应该全国推广的,有埋汰说要是有了两杆枪怎么说也要找两个洞的。个个的电子喉咙都挤出破音的嘎吱声,简直是群魔乱舞,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跟他们有仇。我在思维里调出iface的界面,选了个面有愠色的表情,吼了声,“你们倒是把医疗单给老子收起来啊?铝面硅字,又是二号字,闪闪发光得我隔个老远都看得见!”——《国生育恢复办省组鉴定室公民(男性)生殖恢复配型报告》。
这群王八蛋笑得更放肆了。商陆一挥手,说,“沙舟要起锚了,快上船。大家就别洗刷他了,真让周围的姑娘或者爷们知道了这家伙能配种,我们几个缺胳膊缺腿的,挡不住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懒得搭理,扮出一脸无烟无火。实际上得知能成的刹那,脑内资源管理器已经报警多巴胺分泌过量——“是否进行内环境调整?”“受体靶向阻隔预备中……”的对话框铺天盖地地泛滥着。早知道叫人帮忙ROOT一下下丘脑并行系统,不然迟早被各种提示烦死。
紧接着,心血循环系统弹出警告,我还没来得及查看,视野里啪的一声蓝了屏。随后是内置心脏起搏器的充电声,放电声,还有维生辅助系统输送营养液的悉索。
再次睁开眼,是深邃的夜空,众星簇拥着幽蓝的“恶魔之花”,对视我。耳后是硅晶与碳沙的摩娑,断然是在一艘沙船上了。我撇开头,撞见商陆那张合成脸。
“我倒了多久?”
“个把钟头吧。能装个那话儿就把你激动成这样。平时也不自我检测紧急辅生系统。重生科技早就发过通知,不自检系统,要是像这样激动死了,一分钱的保险费都没有。”
听到这种话题心里就一阵烦躁,我又把头转回去看天。天上有三个红点闪烁着飞过,兴许是军方的喷射机。在此个瞬间,我突然希望它丢下一颗大炸弹,熊熊烈焰把我焚个干净……因为下循环程序提醒我,由于重启动造成的紊乱,人造尿道阀放出了一些液体。
烦。
所以,我说,“好啊,死了多好,我倒给人保险金让我死逑中不中。”
“你这话,不爷们,蔫了才几年,就躺在地上打滚撒赖。我叫其他人先去你家把好消息告诉你爸妈了,估计已经摆好宴席,你马上就能变回千里挑一的真爷们了。别哭丧个脸,来,整个口香糖。按你的要求,我又找了一个牌子的,看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
我支起身,接过口香糖。说了声谢谢。
拆开包装,塞进嘴里。那么一瞬间,口腔内充满了她独一无二的香甜。伴随口香糖的滋味从口中蔓延,一种视觉上的空白也以我为中心扩散到无限弥远——埋没了岸,灯,碳沙和船的鲸群。在这不真实的白境里,我看见,麦田荒芜,群鸟长出一身锋芒,一条蚯蚓从初生的男孩的嘴里爬出来,而一片小雪错嫁给了春天的诗人。
“商陆。”
“嗯?”
“这口香糖哪买的?带我去,现在。”
“开玩笑吧你。”
“没有。我找到周茜了。”
2.
我在铁下心宣布那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茶几上的盘子里是瓜子,开心果和削开的苹果。苹果的果肉正在渐渐变色,一片瓜子壳掉在我的鞋子里,脚踝的设备管理系统开始不停弹出报错提示。
我的左手边,亲戚和朋友们在传看我的“恭喜成为国家种马”的报告,我之前试图跟他们谈谈战后如今世界局势的话题,不过似乎他们对我本身的兴趣超过了这个星球的未来。在我的右手边,母亲在掐我的手臂,就像过去的二十二年一样。不过她似乎没注意,她掐的硅胶层下面不再会有神经末梢,并不能起到提醒我的作用,自然她也没法继续推销那位“军区医院说了,身体存有率59%,子宫好端端的”的好姑娘。在我的前面,茶几与电视之间,父亲穿着老军装,抱着麦克风,把自己的电子喉咙调成了蔡国庆的声色,在唱《今夜星光灿烂》,自得其乐。
我站起身,眼光落在白的墙壁上,没有看任何人,大声地说:“我已经把申请交上去了,我现在只需要等政府的回复。我已经决定要跟谁结婚了。”
四下无声。
隔了一会,父亲转过身,两只红外义眼锁着我不放:“你说什么。”
“我说,我已经决定跟谁结婚了。”
“谁?”
“一台口香糖售卖机。”
“……”
母亲哇得一声哭起来,双目涌出大量人造泪水,两只手气得直拍大腿,对着父亲大声哭喊,“他又来了!又这样了!”父亲丢开麦克风,两眼红光骤亮,身子嗡嗡作响,他转身走进卧室。他的表现让我感到强烈的不安,卧室里传出翻箱倒柜乒乒乓乓的声音,情急之下我像机关枪般扫射出一大堆话:“爸!听我说她不是一台机器,我是说她是接在那台机器上的人脑主机!咱们家在军区医院认识那么多关系,给她装个身子没有问题!我在战前服役的时候就认识她了,她叫周茜是一个医务兵她喜欢口香糖,我和她亲嘴都是口香糖味!这虽然听起来很扯但是我敢肯定那台机器就是她做主脑的——”
父亲拿出一个初始化U盘,冲着我,像举着一把血淋林的刀。母亲哭得更响了,骂着“死老头你这么搞何时是个头?”,又扑向我说,“小商你什么时候当过兵?你从来没有当过兵!你怎么会认识一个叫周茜的女兵?”
我一时间大脑当机了,说不出话。父亲趁机猛地冲了上来,抬腿踹开茶几,瓜子开心果苹果上的全息影像通通失灵,露出微生物合成胶冻的材质,被父亲一脚踩下去,流出油亮的汁液。
“跑!”
我越过一众目瞪口呆的亲戚朋友,往窗外爬去。假瓜子壳造成的报错糊满了视界,什么都看不见。一咬牙,我用手护着头,对着玻璃窗纵身一跃。
在坠入窗外那条沙河之前,我听见母亲的呼喊。
商陆!
商陆!
3.
我叫商陆,二十二岁。在决战到来的一年之前,我在军队里服役。体检的时候我认识了医疗中尉周茜。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她,同时喜欢上她的还有全连83位战友。但是她最后喜欢上的人是我。时至如今,我已经想不起她的笑容,她的发梢,只能想起在第一次亲吻的晚上。我们两个沿着机场的铁丝网走着,她转过身面对着我,捏碎了手里的蒲公英,战机正在起飞,风裹挟飞蒲拂过我的脸庞,引擎巨大轰鸣声里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最后她扑过来抱住我,我亲吻着她,嘴里弥散开一种让我深陷的独一无二的甜味……
终于到了那天。
防空警报凄绝的嘶吼着,随着一道闪光,蓝色的极光般的花在夜空绽放。物质破坏性转换的开始,半导体开始崩解,防空警报便呜咽了。水泥路面崩裂,瓦解,高楼大厦崩塌,粉碎,都化作黑色的碳沙海洋。地上奔逃的人们,包裹在天地间绝望的黑色里,五官从脸上滑落,内脏从千疮百孔的腹腔流出。血凝固成碳的粉末,飞散在狂风大作的空中,飞跃硅晶化的树木,扶摇直上。
一个人,拖着半融化的身体,缓缓蠕动着。他看着怀中的女人渐渐消逝,只剩下一块灰色的脑组织。人类的最终兵器让他已经分不清黑与白,是与否,情与爱。他看不见,听不到,嗅不得,摸不着。一切生而为人的外壳也已溶解,换个说法,他也只剩下人类的残渣了。
然而他还要活。
衣服融化了,脸融化了,口腔里残存的口香糖融化了,一滴一滴,落在不成形的手上,落在手上那块曾经爱过的人的一部分。
饿啊。
他张开嘴。咬。
咬。
咬……
4.
等我醒来,眼前已是躺在省医院手术台。
透过视界的管理员调试界面,我可以清楚看见面前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她有一颗半原生半合成的头,头发亦是一半真发一半假发,很可笑。在她的左胸,上面挂着一块名牌,上面写着:周茜。
周茜是一个滔滔不绝的研究员,很明显,她平常没有什么机会抓到一个人听她扯淡。哪怕现在在她面前,是一个身上准确的说只有一个大脑,一片嘴唇,五节脊椎,一对睾丸属于人类的混合系统,而且这个玩意主系统已经关闭,等待进行海马体重置处理。
她对着我的眼睛或者说光线感受单元笑了笑。鉴于她特殊的头部构造,真的只能说狰狞极了。
她迎着我的厌恶的目光,毫不客气地开口:“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说我长得丑?没关系,大家都长得丑。在物质转换武器发动的瞬间,第一个被消灭的就是美。现在的人类不过是战前人类侥幸的残渣啦。”
“残渣,你好。”
“回敬回敬。”她轻快地敲着键盘,不以为然地说,“其实残渣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我就没有一对能够通过渠道提前知道决战到来的军领导父母,也不会有财力有手腕把拿去当人肉单片机都嫌不够的儿子躯体残渣强行续命。”
“……那么为了公平,请务必把我做成一个汽水售卖机,放在一个口香糖售卖机旁边,谢谢。”
她先是一愣,随后大笑了起来。一开始抿着嘴笑,后来捂着肚子笑,一边笑一边砸桌子,笑得半边脑袋跟着发出咔咔的金属怪响:“哈哈哈!海马体真是个好玩的东西,捡到啥用啥。”
她扶着桌子咳了两声,滋啦滋啦地,又扯开破锣嗓子:“看在你又要被重置的份上,我再告诉你一次。你的脑组织根本没法复原成一个正常人,甚至当单片机都不够。要不是你有一对可以用来繁殖的睾丸,于公于私,你现在都该在回收桶里发臭。你是我们最后采样了若干其他人的灰质,像拼百衲衣那样拼出来的。本来一开始你运行的挺正常的,结果可能是某个人的灰质的刺激很强烈,导致你想象了一个苦苦寻找的战前女朋友,叫周茜——你幻想你服过役,也许是出于对父母的崇拜,或者某个灰质的主人是军人吧……人的大脑存取记忆实在是乱七八糟,这调用一块那调用一块。”
我默默地看着系统调试选项在她的操作下快速变动,无话可说。
她见我无动于衷,眯起眼,把那鬼脸凑过来,“再说说你幻想的那个可怜的罗曼蒂克,也许战斗机起飞来自某个宅男对军事视频的回忆,风是一位农民耕作时感受的烈风,蒲公英来自一个小屁孩的郊游……口香糖就只是那种廉价的口香糖而已。你爸妈跟我说,你还以为你的女朋友'投胎'成一台口香糖机器?哈!真亏的你能想的出来——”
“闭上你他妈的臭嘴!”我打断她,去他妈半张脸的八婆。给浑身的合成肌肉灌满液压,我猛地挣脱了手臂上的束带,起身匆匆冲出门外,她刺耳的嘲笑仍在深长的走廊上阴魂不散。
“那些记忆都是你的,也都不是你的,可怜虫!”
5.
街岸上低压钠灯开放着光的蒲公英,硅晶沙船在黑的旷阔的碳沙上起伏,犹如泛着金属光泽的鲸群。
找对了。
我来到一台口香糖售卖机面前,坐下来。那是一台很简单的自动化机器,只链接了一位培育在维生系统里的人脑。那是一团泡在充满营养物质的玻璃罩里的人脑,放在机器顶端,没有名字,只有铭牌上一串代码。决战留下了如此众多的人脑,以至于它们代替了所有本属于半导体芯片的工作。看着那灰质上的沟壑纵生,那充满细小气泡的绿色凝胶,一种巨大的距离感,像刺刀一样,抵着我。
我偏了偏头,看见商陆的机械脑袋。他还是以往那样,顽固的很,都成了合成人了,那身破破烂烂的旧军服从来也没脱过。除开一个大脑,一片嘴唇,五节脊椎,一对睾丸以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他苦笑说,“你真是脑子坏了。”
我说,“彼此彼此,商陆。我们找了这么多年,你确定她真的是周茜,没弄差了?”
“不会错的,我都信不过吗?看这额叶的回路形状,和捧在手上时一模一样,把她接到合成义体上,她还会是活生生的那个爱吃糖的医疗兵妹子吧……”他说着说着,噎梗了。商陆和我一样,坐到了口香糖贩卖机旁,他把手环在机器的后面,仿佛搂着他心爱的人。贩售机的电子彩灯在液体的折射下旖旎变换,我恍惚间看见,在绿莹莹的玻璃罩上映着一个女人的纤细身影,旁边一个男人又好像是我,又好像是商陆,搂着她。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周茜在我怀里,倚靠着我的胸膛,我和她都穿着破旧泛黄的军装,尽管那场战争(已)成风沙远去了多年。扑腾的鸠鸽与郁金香花瓣在我们的婚礼上飞舞,我为她的鬓发上别两支金黄的蒲公英,她笑嘻嘻地拋下手里的花束揽住我的脖颈,柔软的嘴唇贴上了我的,耳边是礼钟乐响,欢声笑语。
第二天早上,我的身边没有了女军医,没有了机械老兵。我只听见警笛和喧哗熙攘,周围一圈人围着我,一部分是我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一部分是警察。我是被其中某个性急的条子推醒的。
我一醒来,就看见穿戴正装的父母怒目而视,母亲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批“商陆你都二十多岁了,还疯疯癫癫地乱跑?问护士也说突然逃出去了不见人影”跟着父亲注意到我怀里抱着的周茜,气得面色发青,嘟嚷着“真是丢人现眼。”
经过商量,警察和寻人的亲友被父母客气地送走了。在我的拼命要求下,我不顾旁人惊诧执意把口香糖贩卖机买了下来,推上沙舟,搬往家里。一路上父母不断盘问,我口中的那个周茜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当兵的商陆又是怎么一回事……最后他们打电话回去问了医院。
“所以说周博士,这个合成义体里的到底还是不是我这个儿子商陆?”父亲抓着手机黑着脸,要吃人似地逼问电话另一头束手无策的研究员。母亲拽着父亲的胳膊一旁劝:“人回来了就算了。当初能保住一部分大脑和生育能力就不错了,天有不测风云……”
父亲气势汹汹,又指着我身边的周茜厉声问:“听着商陆,要真要娶这台机器别的不说,怎么传宗接代?为了一个别人记忆里的女人,值得么你?”
“把我的睾丸,我的大脑拿去克隆代孕,试管婴儿什么都好。”我一咬牙道,“以前的商陆只是现在的我的一部分,不只有以前那个商陆的意识记忆了。”
“这孩子脑子坏了!彻底疯了!”
父母亲眉头深锁,两人激烈讨论一番,最后无可奈何地认为,我,商陆大脑复合体1号,是个无可救药的失败实验体。他们决定,属于商陆脑组织的一部分他们保有原型,然而必须得把我的睾丸,嘴,五节脊椎回收,重新匹配给新的商陆实验体。
母亲流着泪,依依不舍地追问,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盼我能回心转意:“可你呢?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也是我们的儿子商陆啊,都回家那么久了,总不能把你就这么处理吧……”
“那么,妈,请把我做成汽水售卖机,放在那台叫周茜的口香糖售卖机旁边,谢谢。”我重申了一遍起初跟护士说的话。
6.
我是商陆,现在是一台汽水售卖机,兼职商陆的备份记忆体。我的旁边是一台口香糖售卖机,她曾经是我的爱人周茜。我和她被安置在商家的私人沙舟甲板上,平时只有我的继任者商陆2号操纵着合成义体和他的家人使用我们,生活十分悠闲惬意。
我们每天都会一起在船上看日出和日落,黝黑的砂浪滚滚地淘洗着木制的船底。随游的巨鲸偶尔用尾卷起一拨砂砾,洒在置放她跟我的甲板上,在我们的玻璃窗或金属板上磕碰出清脆的弹跳声。我和她在日常交通下随着风波跌宕起伏,风和浪就会使得船体摇晃,不一会我与她就会被推并到一起,不一会我们又会随着颠簸暂时分开……
我和她被好心地安装上了最前沿的智能售货系统,所以我们可以发声闲聊。比以前有义体的时候不足的是,不能随意移动。
周茜只能听懂简单的对话,因为她也是临时拼凑成的脑组织,只考虑到了做最基本的售卖功能。她说,她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但是她记得她以前有一个爱人,当过兵,也喜欢吃口香糖。此刻一阵强风吹过,将我往她身上推去,我趁机刹住底下的轮子,紧紧贴住她,我们两台机器恰好被卡在了一个转角处。
如同在梦里,我梦寐以求地同周茜拥抱在了一起。我忍不住震动了一下,一瓶饮料从货架上掉落到了取货口,通过我的扬声器,我在她的麦克风旁边悄声说,傻瓜,那就是我,我终于找到你了。
她发出咔咔的电子杂声,似开心地笑了:“谢谢…咔滋……咔…惠顾。”
© 本文版权归 荒远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及合作请联系作者。
原创文章,作者:荒远,如若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