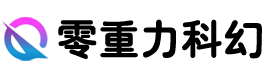作者:不暇自衰
责任编辑:旅鸽
本文获得第五届衬衬杯科幻征文三等奖
导读:孤独的列车在核冬天降下的冰雪中漫无目的地前进,本就稀少的幸存者却在不断失踪,毫无疑问,列车上混进了感染者,在这绝境之中,我到底会成为猎物,还是猎人?
一
发现血迹是昨晚的事情,道林所在的车厢里空无一人,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毫无疑问,有感染者混进逃亡的队伍,在夜里张开了獠牙。根据病菌特性,它会不断地侵染健康人,直到改变他的身体结构与大脑,所以列车里的乘客必须在到达光明之地前,清除所有的感染者,决不能让病菌被列车带到人类最后的净土。
最近几天失踪者很多,原先拥堵不堪的列车里只剩下十余人,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占用一节车厢来用作房间。一开始是为了避免出现病菌大规模扩散的可能性,才将所有人分散开。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感染者去偷袭正常人,那么对方将孤立无援,甚至毫无察觉地被感染。
至于我,末尾车厢的住户,其实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地方。我能登上列车纯属运气,几个月前和我同行的几百人全部死在核冬天的冰雪里。不管是被感染还是迷失在外面的黑暗里,对我来说只是不同的归宿而已。
我可以打开车尾的铁门,虽然每看一眼外界都要承受极端的寒冷,还有对身体造成伤害的辐射,当我每次望向那些隐隐翻滚着的乌云时,总在期待会不会有一丝光亮能温暖苍白色的大地。虽然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答案,但是列车里每个人都说,光明之地科技水平很高,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驱散云层,消除辐射,而且到达那里后,就不必再忍受饥寒。
尽管我努力去相信,但在列车一直行驶了二十几天后,光明之地越来越像一个虚伪的谎言。
吃过简单的午餐,列车长刘先生送来了一些武器,不过都是小刀、长棍之类的,用途十分有限。我知道他腰间有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但在他死之前其他人还是拿不到他保命的玩意。
所以也许这就是他在接下来两小时后,就死在所在车厢的原因吧。
没有人听见枪响,更没有打斗的声音,只有一位女士惊恐地说她闻到了新鲜的血腥味。当刘先生所在的车厢被撞开之后,我们看见地上仍然温热的血液,和他被割断颈动脉的尸体。于是所有人再次聚集,我记住了这位女士的名字,她叫凯琳,我得提防她。
最后是叫做亚奇拉的年轻人取出刘先生的枪,说只有他拿着枪才能保护列车上其它人,亚奇拉也规定自己每天会定时巡逻,对抗感染者。
我注意到他嘴角难以被察觉的微笑。
二
隔着车窗玻璃,凝结的冰霜遮挡住外面的一切,见到阳光是多久之前的事了?我已经完全忘了。在我残存的记忆里,圣洁的白云点缀着深蓝色的天空,柔和的光芒播散全身,我仿佛沉浸在温暖的液体里,舒适而满足地享受,直到闭上眼睛。
光明之地对我毫无意义,我只想回到从前,不想前往面目全非的未来。
我将随身携带的匕首固定在长棍顶端,用胶带一圈一圈缠紧,然后把这个简陋的新武器绑在后背,刘先生之前分配的小刀则被别在腰间。身上的衣服很厚重,虽然影响行动但是足够暂时抵御外界的寒冷。深呼吸之后我打开后面的车门,然后熟练地跳上车顶,凌厉的风就像刀子一样刮过我的脸,靴底的长钉无惧顶部的冰雪,但是我的脚步依然很轻,以防被人察觉。
道林不是我杀的,他的尸体肯定已经被扔出列车,不过我大概知道哪些人是伪装拙劣的感染者。
在车顶行进的过程中,我的脚下出现一些凝结的红色,也许是我之前行动无意留下的,但更有可能是那些感染者所留。他们畏惧潜伏在列车里的杀手,尽可能地伪装自己,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夜里杀死或同化仅存的普通人。不过列车上也只有几个可能的目标,感染者迟早会露出马脚。
过了几十分钟,在只剩下风声的黑暗中,我凭着直觉停下脚步,蹲下身看着透出亮光的车窗。车顶有许多可以固定绳索的金属装置,我只有用衣物制作成的布条,但也仍然足够支撑我的身体。
随后,我突然倾斜,坠向列车一侧,绳状布条将我拉住,这惯性使我贴向车窗。我已经双手紧握住之前的武器,借着这力量用锋锐的尖端刺向身前。一声脆响之后,玻璃出现细密的裂缝,随后猛然碎开,我直接翻身而入,里面的凯莉刚坐起身,喉咙就被尖端的匕首直接刺穿,仅挣扎几秒钟便没了声息。
我上前拉开她的衣袖,手臂上出现我意料之中的紫色血点,那就是被病菌初步感染的象征,这个人并没有失去自我意识,也不拥有感染者的力量,现在杀死最为合适。
我随手将尸体扔出窗外,一声沉闷的坠响后就再无声息。我反锁住这节车厢两端的门,简单的让身体回暖放松之后,拉住被风吹进来的布条,然后离开这节车厢。外面的风雪很大,几个小时就会消除我的脚印,只要不留下痕迹就没人能查到我的身份。
列车里有些人的失踪,是我造成的。
三
昨晚有两人消失,列车只剩下九个人,他们神色各异,有些脸上只有畏惧。亚奇拉把玩着手枪,高抬起头注视着每个人,脸上只有虚伪的歉意,我从他的眼里看到毫不掩饰的轻蔑。
“对于昨晚的事情,我感到很抱歉,是我没有尽到保护大家的责任,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别对我有太大的戒心,每个人的房门竟然都紧锁着。你们得知道,我总不可能强行破门而入。”
他说完这些话,将手枪放进口袋,我注意到角落里一位老妇人在止不住地颤抖,昨晚失踪者之一就是她的丈夫。
亚奇拉背靠着墙,我的神色似乎不够让他满意,于是他喊道:“角落里那个瘦子,你是谁?”
很明显他根本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我也不想让他知道,不出意外的话,我会让他消失在黑夜里,尽管可能比昨晚那位困难一点。
“你没必要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保护。”我以微笑回敬。
“我想起来了。”他的神情微微变化,“你住在最末尾的车厢,那节车厢可以打开尾部的车门,这样你可以通过车顶,来到达任意一节车厢杀人,我说得对么?感染者。”
“只要花时间同样可以拆卸每节车厢的窗口,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车顶,但你认为有几个人可以忍受现在外界的寒冷,你怎么知道通过车顶可以杀人,你上去过?”我平淡不惊地反驳。
他突然拿出手枪,指着我说道:“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将你隔离,这是大家的意思。”
“应该把手臂上有紫色痕迹的人隔离。”我举起双手,变得面无表情。话音落下的时候,有几个人的呼吸在那一瞬间急促,我迅速记下他们的面孔。不过现在,亚奇拉已经把我视为眼中钉,因为除了不在场的列车长,我是唯一反抗他管理的人。
亚奇拉很可能会在今夜将我变为目标,但是他很早就是我的目标。
谁会死呢?
四
我被绑在靠近车头的那节空车厢,手脚都被绳子勒住,眼前的地面上放着一些食物,内部很空荡,也很黑暗,以至于我无法推测时间的变化。如果我要吃东西,姿势肯定会显得很屈辱,但是没有力量也就对抗不了晚上的亚奇拉,以及更多的感染者。
我猜,亚奇拉起初就是唯一的高度感染者,不过现在病菌正在扩散,他杀掉对自身有威胁的,感染服从自己的,一步一步同化入侵整个列车,或许还会用相同的办法渗透光明之地。
其实我认为未来的发展会更为有趣,但由于他过早注意到我,所以今夜会不可避免成为决战的时刻。他想着杀死我,将我扔出车窗,然后就能把我伪造成逃离列车的唯一一个感染者,来安慰其它只剩下恐惧的普通人,让他们更不容易反抗。
我是不会死的,作为几个月前雪地求生队伍的唯一幸存者,作为这列车上唯一的猎人。
“我们会离开这里吗?”
门后传来轻声低语和几个人的脚步声。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权限,只要清除掉所有可能的威胁。”亚奇拉的声音也出现了。
随着齿轮的旋转,微光从外界进入车厢,但很快被人影遮挡。亚奇拉走在最前面,紫色的脉络一直蔓延到掌心,昆虫口器一样的器官很快形成,从中出现布满倒刺的细小触手。而其它人显然没有达到他的程度,但病菌聚集体仍布满了他们的瞳孔和手臂,在白色的皮肤上显得突兀且让人恶心。
我抬起头注视着亚奇拉,没有丝毫畏惧,甚至有些轻蔑,就像之前的他一样。
“杀了他,这样的人没有时间去感染。”
他似乎畏惧我这样的神色,所以很快下达命令,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位老妇人拿着刀向我走来,她的袖口隐约看到病菌侵染的痕迹。昏暗的车厢内,她的脸色显得异常苍白,身体仍然在微微颤抖,不知是激动还是恐惧。
“对不起,孩子。我们也只是想要活下去。”
并不锋利的刀尖直接指向我的颈部,与此同时我也看见亚奇拉也将手枪对准我,也许他们早就怀疑我是杀手了,才会如此谨慎。
下个瞬间,时间都仿佛停滞了,只剩下老妇人落刀和刺耳的枪响声。温热的血液让灰白的衣服变得更为肮脏,更多的液体喷射而出,在地面汇聚流淌。在所有人暂时的呆滞中,我推开老妇人被子弹穿透,又被匕首刺穿心脏的躯体,手中自制的武器迅猛一挥,打落亚奇拉的手枪,然后露出让他们惊慌的微笑。
“你果然是猎人,我们寻找很久了。”
亚奇拉向我冲来,被病菌赋予的身体素质异常惊人,锋锐的触手在我的肩膀留下一道长痕,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我撞飞。我的武器为了抵挡一部分攻击而断裂,还粘着胶带的匕首在地面叮当一声没了动静。
在求生队伍里,有人告诉我,病菌是参与战争的一个国家研发的,目的就是将敌对的军人和平民变为绝对忠诚自己的战争机器,可在还没有完全制造成功的时候,初步品种就在研究室发生泄露,成为了核冬天之外,另一个对人类有效的大杀器。
“我只是为了救赎你们,可是总有些家伙依旧愚蠢。”
五
我很快爬了起来,除了肩上的伤口在流血之外,大脑也因为之前的撞击显得昏沉。放在口袋的小刀被我拿出,我摆出防卫的姿势,很快就有一根触手向我扫来,被小刀直接切断,随着又一声枪响,子弹穿透膝盖,剧痛让我难以忍受。此时我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病菌似乎正通过肩膀的伤口将我变成感染者。
刺耳的刹车声也在响起,列车减缓了速度,竟在这冰天雪地中停留。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光明了,天空永远是灰色,时不时落下肮脏的雪花,我曾经想要去否定这个世界的存在,但是却只能明白自己的无力。现在我仍旧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可并不代表我会甘愿保持现状。
我没有倒下,凝视着走来的众人,他们都是奴隶,以解脱的借口被亚奇拉完全控制。在他们向我扑来的刹那,我突然一跃,撞破本来就松动的窗户,外面的绳子在晃动中被我紧握,寒冷从伤口中涌入我的身体,外层的血液瞬间凝结。亚奇拉扣动扳机之后射出的子弹被我侥幸躲过,我顺利的到达车顶,浑身都在不停颤抖。
其实我已经猜出来,亚奇拉是故意让我逃出来的,也许是为了看待猎物挣扎的乐趣,或者是其它让人厌恶的原因,可能对于他而言,我从猎人变为猎物那一刻起,才是他最兴奋的开端。带刺的触手伸了上来,尖端直接生长出利爪,而正中心是一只黝黑的眼睛,病菌很显然完全占据了亚奇拉的身体,以至于人的形状也只是一种伪装,他完全变为另一种生物了。
“来吧,我们看看谁是猎物!”
我紧握小刀,直接跳下火车,随着耳膜的嗡嗡作响,全身都陷入雪地。庞大的身影也从身后落下,遮挡住火车窗透出的微弱光芒。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亚奇拉的声音随着身体的变形而扭曲,“你可以现在选择服从我,我能给你病菌的全部力量,如果你拒绝,我将会杀死你。”
“虽然我不清楚,你为什么把我称为猎手。”
我从雪地中站立,摇晃着向他走去,脸上有着疯狂的笑意:“离上一次绝境都过去几个月了,我一直活着,所以现在我仍然不会轻易死去。我知道你还残留着一丝恐惧,那一只猎杀感染者的部队应该在你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你用不着恐吓我,那只部队没有幸存者,而你更不可能是。”
“为何我能在冰天雪地中活着?”我抬起手取下手套,注视着苍白的皮肤上,紫色的脉络在迅速蔓延开,就像树根的生长,又或者是肆无忌惮的真菌,侵占所有正常的血肉。
“你口中的权限,是什么意思?”
我的瞳孔也在黑暗中变为紫色,耳边的伴随列车的刺耳刹车声,全身的伤口都被强行闭合。病菌确实泄露了,但是那些研究员并没有放弃研究,他们明白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所以希望能制造病菌的完全体。他们自然是成功了,成品被注射进一千多名死刑犯体内,让其拥有可以对抗感染者的力量,不具备传染的能力,而且对于国家绝对服从。
那只由死刑犯组成的部队湮灭于最后的核弹定点攻击,而有一位幸存者,奇迹般将体内所有的病毒,甚至包括他的部分记忆,全部转移给一个被辐射严重侵染的孩子。他带着对于国家的服从逝去,而那个将死的孩子得到新生。
我是那个孩子,所以我终究会是猎人。
六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感染者更能适应现在的环境,并且仍然能保持部分人的特性,在这个大灭绝降临的时代,也许人类已经没有能力传承曾经辉煌的文明。光明之地是一场梦,可以让幸存者坚持着活下去的梦,而这列火车只是在漫无目的地行驶,直到再也没有可以补给的燃料与食物。
但是人需要有活下去的理由,哪怕是苟且偷生。
病菌可以通过感染来传达每个个体的记忆,并且感染者之间也可以建立共享的记忆储存,我畏惧使用病菌的力量,并且坚信自己仍然是人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人性正在渐渐散去。为什么我可以在那场冰雪中存活?在我失去意识的时候,身体被病菌控制开始吞噬所有同行者的尸体补给能量,当我苏醒的时候,他们的记忆让我差点失去自我,也让我明白这世界的真相。
亚奇拉很难缠,和他的战斗完全依赖本能,病菌控制了我大部分的意识,以至于我无法了解细节,只能察觉到身体的损伤和嘴里的血腥味。无数的触手被我撕裂,而我被病菌保护的皮肤也被割开,流出紫黑色的液体,又迅速被风雪冻结。
车上的其它感染者全部冲下来扑向我,有些人仅仅是初步感染,思想依然和人类无异,可是他们已将病菌视为生存的信仰。我也许不是他们的对手,甚至可以说我与感染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敌人,可是那一丝人性却始终纠缠着,让我成为冰天雪地中唯一的猎人。
有些记忆涌入我的大脑,原来有一个完全有感染者组成的文明正在建立,它显得稚嫩却无比适应现在的时代,加入的唯一要求就是成为感染者,这就是亚奇拉口中的权限。
这世界没有人类的光明,只有感染者的。
虚弱终于开始到来,有许多触手穿透我的躯体,让我逐渐失去力量。可是我却听到一声声枪响,那似乎是火车上的普通人反抗的声音,直到最后所有的声音都完全消失,只剩下我躺在冰冷刺骨的地面,仿佛不再拥有任何力量,又仿佛在等待死亡。
“本就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有认同和抗拒。”
不知是谁在我的大脑中开口,让我猛然睁开眼睛,身体没有任何痛感,只剩下寒冷。我无法动弹,因为肌肉都已经结冰,而大脑也处于思维缓慢的状态,不过随着意识的运转,温度在渐渐的提高。
列车已经远去,周围有许多血迹和残尸,它们上面都覆盖着浅薄的白色雪花。
我很久没有看到白色的雪花了,这纯洁的颜色是这灰暗世界唯一的美,它让我的嘴角露出微笑。等待许久之后,我站了起来,身上的衣服碎裂成布条,随风飘荡,阳光依旧没有出现,可是我却感受到莫名的温暖。
地上有一把手枪,我捡了起来,然后对准自己的大脑,这是被病菌完全感染的人唯一的弱点,可能我依旧不会死,但是大脑中属于人类的部分,会被永远剔除。这对我而言与死无异,下一次睁开眼睛,作为人类的我早已消失。
我还在微笑着,就像情绪都被温度凝结。
这瘆人的微笑啊。
© 本文版权归 不暇自衰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及合作请联系作者。
原创文章,作者:不暇自衰,如若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